嘴边的口头禅:好的绘品艺术的山水与现实的山水总不是一回事,红楼梦的开篇曾说“假作真是真亦假”是很有哲思意味的话语,我们园林的假山,其实是立体的艺术品,源于对真山水的模仿与缩小,当然还有盆景,皆是这类艺术的模仿,但是宋代山水画中的山水仍然与前面两类艺术形态有所区别,它是平面的,这样我们与宋代山水与其之前的不成熟山水与后代变形写意的山水的比较起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宋代山水更接近现实的真实,但是只能是看起来是接近现实的真实,而且我们还要说的是山水与人物与动物之类的作品的区别是,人物与动物对于造型有其严格性(鬼怪除外),人物与动物是生长的,事实上现实的山水也是变幻的,所谓苍海桑田便是这个意思。但所谓的人物绘画,不谈现代的毕加索之类的面的转换(正面加侧面),基本是一个角度与年龄段的再现,在随类赋形的要求上相对于山水画,应当严格些,这样山水画的松散性为这东方古代山水的描绘增添了一种随意性,这种随意性自然亦加强了艺术家(绘者)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因为有这种主观能动性(宋代人当然不懂所谓的马列哲学)宋代绘者天然的运用了这种主观能动性,他们是源于对真山水的认知,同时又不拘于真山水,有所取舍,有所综合,有所集聚,进行了以自己的心相为中心的艺术性的重构。范宽的《雪景寒林图》郭熙的《早春图》等作品中的山水,有气势,有气氛,有灵气,有元气,有气场,甚至有磁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仅仅是前者有寒寂的感觉,后者有温馨的感觉那么的简单。与今天的油画再现的真山水相比,或者直接的用摄影的“真”山水相比,宋画山水的现实主义仍然是不够完美而且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知道的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宋代成就与完美性不是西画甚至摄影艺术所能够比美的,或者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西画甚至摄影与宋画的山水不是一个级别的,没有可比性。
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后还有一句“无为有处有还无”,我们观看自然的山水有一种状态下可以感觉一种“山色有无中”,这就是在有云雾的情形下的观看,那么“云雾”,就是自然山水中增添艺术性的法宝。我们因此感觉真山水进入“艺术”的状态,我们感觉的是“隔离”,是“飘渺”是沉入梦境,或者是进入蓬莱阆苑的感觉,所以我们现代的表演艺术,总是人工造点烟火,让舞台进入梦境与幻境,拉开生活与艺术的距离。那么宋代绘画的魔力是如何形成的,我想除了当时绘者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时代的消磨的原因,尤其是绘制在布面(绢)上的作品,泛黄而有一咱历史的苍桑感觉增添了这种艺术性,这是所谓的云雾与烟火不能给予的,这种历史的苍桑,不仅是体现在宋画中,当然亦体现在其它艺术,古代的书法,瓷器艺术中。抛开这些历史老人的巨手力量不说,单单谈宋代绘者的构境技艺,应当是让人折服的,而且北宋与南宋的山水构境总有所区别,北宋的往往是巍然,高大,雄伟,很有一种力量感,而南宋地偏隅,往往是一角,半边,气势减弱,这也是马夏展示自己的现实环境,那幅著名的《溪山行旅图》能够让人感觉的是人生如寄,过客一行,而强大的山川往往在寿命上长于他们这群渺小的人类,这群渺小的人群又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以少喻多),绘者所绘的山川气势,恢宏程度,绘者的“真实”刻画,山石的质感,不过是加强这种对比,你绝对不会在一个角度找到宋代绘者所绘山水的原址或者原角度,这只是西画的方式,东方绘画的方式其实是游目意足,面面具到,想象力占了主要的位置。关于具体分析著名的宋画山水,我其实曾经有过简明的文字,这里再引用一下: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范宽《溪山行旅图》欣赏。图写雄峻高大的秦地山川,上部主山巍然,中有烟云锁其腰以增的高峻之势,一瀑流从右边石隙中飞流下,如银河落九天。近处为奇石土丘,林木蓊郁,亭阁俨然,中有溪流潺潺,右下一队行旅,渺小几不易辨,彰显山之雄浑巍峨之气象。真有悠悠天地,小物孤然之感。此北派之宗也。
宋代的绘画,在山水画领域,达到中国绘画的高峰,留下不可多得的精品,应该说是之前的绘画历史积累的结果,在英国的学者贡布里斯的《艺术与幻觉》里,谈到绘画的历史非画人所见,而是所知。美国的学者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里同样谈到画人沿袭前辈的预成图式的修正。对于画家的创作绘画是“视觉的眼”所为,还是因为历史传承的结果,愚以为两者皆有之,对于不同的画人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国画人外师造化,并不等于没有师承前代的画迹,应该是不断地游离两者之间:师古人,师造化。在师古人的过程中,民族的特性是会络进后代作品中,在张僧繇时代,西域传过来的西方明暗画风并没有在民族的绘画中生根,而是重视游目骋怀的高远、深远、平远的“不科学”没有“焦点透视”的中国绘画独特“视觉的眼”,用这种特别的“视觉的眼”来察中原山川大地风貌,并展现出来,从早期的“人大山小”的艺术童年稚气作派,到范宽的经典大山巍峨,行人渺小,显示的是艺术的历史成熟,而特殊东方“视觉的眼”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古人的绘画理论领会与画家游历山河的两两相参,造就古典绘画的成熟与后世在某些方面没法逾越的高峰。
一方面画人所绘之山川是传神写照,但你是无法找到古人所绘山川的某个具体位置角度,不象今天画西画那样去寻迹到画家对景写生的位置,这正是因为流动的特别“视觉之眼”造成的,我们东方画家画一个石头,先看其四面,再画出看似一面,实则是综合四面特性的石头,一个石头或假山,放大来就是一个大山,四面看山同样是东方画家的特性,这里又包含历史的传承,古人教我看世界,观造化罢了。表现一个巍峨的大山景致并不是东方绘画的终极目的,最终的归宿是畅神,所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王微语),石涛也说过“世人独以画师论,摇手非之荡吾胸”,所绘山川不管写实还是写意,其灵魂的部分是传其神:文学性,诗意性,哲理性,禅意道气等玄之又玄的微妙不可言说的部分,如说的陶潜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个“忘”字,应该是当找不到解。)所谓“道”不可言说的,具东方思想心灵的同一民族人方可领悟其中的真谛。
东方范式的山水作品最终在近现代被西方画人青睐,不管是国门打开,文化遗存流入西方,还是东瀛人的传播,还是西方人主动的探寻,东方艺术的魔力最终让西人无法抗拒,酿成现代艺术的滔滔洪水。同样,东方绘画因国门大开而染西风,这里,绘画知识的作用由历史的纵线转为平线,师西人师古人,西方“视觉之眼”与东方“视觉之眼”两两混合,这正是今天艺术的普遍现象。
回过头来再读范宽的作品,我们不会以西画的眼光说我们古典的作品透视方法如何的不对,皴法如何的不科学,而是要用游目骋怀的观点,把握画面的总体气象,领悟其中所表现的巍峨壮丽的故园山川情怀:人在旅途,人生如寄,世界如此的伟大,人生如此的渺小,一切俗情便会淡然,获得欣然的快意。
郭熙的《早春图》
郭熙《早春图》写惨淡冬山如睡后的初醒,转为春山澹怡应笑未笑那一瞬间的印象:残雪消融,溪流淙淙,南风轻拂,山涧萌动一种生机与活力。图中远山崇峻,春云锁腰,近丘苍松挺然,杂树枯枝吐芽,半山有楼阁屋宇,山涧有瀑流飞下,汇入下方江潭,右下有行人登山,心态欣然,其形十分渺小,益显山河的壮丽瑰伟。有学者认为郭河阳是中国最早的印象派画家,原因是表现大自然的气节变化,四季的不同景象表现,这不仅体现在其《林泉高致》的艺术理论中,亦体现在其作品创作中,虽然是水墨为上的理念少了色彩的作用,仍然让观者读到四时气象的有别,此早春图的景致如其说的:“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只不过是:“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的状态中刚刚苏醒的那个状态,表现得十分的分明,印象派的画家会画同一个景致的早、中、晚不同时节景象,郭氏作品气魄大点,是四时的变化,但四时的变化又有早、中、晚之分,画家对自然的观察是入微细致的,反映古代中原人的艺术智慧的高明与早熟。《早春图》在整体风范上看有点迷朦的感觉,如山雾盘恒在其中,有湿润的烟雨北山的感觉,这附合当时中原气候的真实状态,过去的中原尚不如今时的寒冷,有现时江南那个时节同质的烟云变灭的感觉,不可以今时的气候衡量古时的气候,这样方读懂画中表现的真实时节感觉。郭氏发展了李成卷云皴为主的艺术风格,图境中能够唤起诗意与云卷云舒,冲远淡泊的士人情怀,有一种难言的魄力。
附文:台北学者李霖灿认为郭熙是最早的印象派的画人,曾画同一地点早中晚之景,实际上他的《林泉高致》的表述能够说明这一点,一个晚照之景便各各不同,一个山景便是如笑如滴如妆如睡,如同欧洲早期印象主义画人一般,同时又重视诗意表达,兼具后期印象主义的特质,可惜木质建筑没能保存画迹,为一憾事也---
范宽的《雪景寒林图》
范华原《雪景寒林图》写巍峨苍莽的北国风光,大气磅礴,境界森然,图中山石高峻峥嵘,主次与层次皆分明清晰,用“雨点皴”表现山的质感,点密密的林木郁郁苍苍,留出空白表现雪色清寒凛冽,其画骨力雄强,描绘细致精到,体现宋画共同的写实主义特点,范氏饱看秦地山川,常浸润其中,得三秦山川之神采。
《雪景寒林图》虽图秦地风光,具北派风范,但并不是十足的北派风格,因为雪景与水墨为上的理念,在王维的南宗中是同样的重视,故在诗意与境界上,融合南派的元素,不可不察,而且图中的萧寒荒古,静穆自然的意味为北派画作增添阴柔的韵致,使雄浑苍劲的北山刚健中含婀娜,庄端中杂流丽。
图中的主峰偏右而高耸,远树密密麻麻附在峰头山脉顺势而下,与近景的寒林相呼应,嵯峨主峰两旁有从山护持,远近层次分明,半山有亭阁半隐半显在岩后林中,山溪从主山两侧而下,时隐时现,左侧山溪经廊郭屋宇下方流入江潭,右侧则流过小桥而汇入潭溪,江潭上有平坡土石,披上银装,增添空灵与亮丽,前排地古林残的寒林清晰有序,根枝古穆屈折,枝桠交叉重叠,密如不透风一般,虽无叶儿,仍显生机潜藏。整个画面布白疏密有致,着墨处与空白雪色处配置适当,画面的雪色迷朦如同氤氲雾气,增添画面灵动与生机,破密麻树点带来的沉闷。
此绢本作品经年代的雨洗风磨,有点古旧,然而观者读画时会有“坐觉苍茫万古意”的感觉,当然是古画相同的物质,只不过对于范宽的《雪景寒林图》更显明显,是墨点密密麻麻与雪景的境界有关。北宋并非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时期,却是一个文化艺术的高峰期,以山水画而言,正是创造有唐一代未能达到的高峰。范宽为代表的北派画人,创造后世无法重复的经典之作,有点象欧洲文艺复兴画家一样,成为绝唱。
李唐的《万壑松风图》
李唐《万壑松风图》承范宽画风,图浑厚崇峻的北国风光:主山高耸,以岩石为主体构成崇峻嵯峨的感觉,上有林木郁郁青青,如黛帽一般,从山瘦削如刀,坚挺向上,直入云霄,如同皇上的侧卫护持,半山中有云烟袅袅,灵动自然,主峰旁两道飞泉直下,几叠过后,汇入下方淙淙溪流,近岩峥嵘万状,坚实浑厚,上有万木蓊郁,一群松大夫错落其间,苍翠欲滴;其山谷松风鸣然,泉水淙淙,静中寓动,刚中有柔。其创斧劈皴以增强山石的质感,山石肌理自然清晰,有四面看山石的浮雕感觉,真为中国古典写实主义画作之经典。此图主峰左侧一从峰有字题云:皇宋宣和甲辰春(一一二四年),河阳李唐笔。为李唐南渡前作品,李唐生活在北地时,北国的崇山峻岭尽入眼帘,故有真感受,阅北山多了自然了然于胸,发而为纸面是“真境逼而神境生”,画之南北宗因地域关系而分源异派,但在李唐的作品中,体现的是南渡后多图平缓的江南景致,且因为流寓异乡而有故国之思,充满伤感的情调与意境,与其图北国风光的雄浑苍劲,阳刚正气的风格相左,李唐南渡后此风几成绝响。
宋代南渡的画人与南渡的诗人一样,有北定中原的雄心又有现实严酷而退隐失落的矛盾心理,南渡后李唐画了《采薇图》、《晋文公复国》、《胡笳十八拍》等作品,寄意遥深,但更多的是《清溪渔隐图》那种渔樵烟雨,山色空朦,水墨淋漓之类作品,写尽失意惆怅之余的淡定心境。强过隔江犹画胭脂色的画人。
李唐的《采薇图》
有的艺术品能够让人开心浪漫,或者快乐,主要是内容与形式而言,如果多买胭脂画牡丹或美人图,当然会有众多的欣赏者,但总有一些严肃深沉的作品,李唐的《采薇图》便是这种有思想内含的画作,表达画者南渡后的忧愁惆怅心理,历史上的伯夷叔齐对于改朝换代是采取抵触情绪的,实际上历代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时,有人归顺,有人隐居,有人归天,成为一个十分正常的保留节目。
图中的两高士处险绝的悬崖峭壁,随意坐在一块平缓的岩石上,上有几株古树护持,一竹器容具是其采野菜的工具置于岩上,岩下远处有溪流回环,所谓“江流曲似九回肠”吧,表达画中主角的心理。高士所背靠的峭壁之用大劈斧皴法,呈现出的岩石肌理,借以表达画中主角的坚毅与沉着,白衣的伯夷叔齐用深沉的墨与色衬出亮度显示其高洁之意。作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最终的结局不好,却成为历代遗民的精神寄托。
李唐那些雄浑的北国风光不再出现在画面,代之以失落的历史往迹来抒发自己故国之思,有时靠画画生存都不重要了,只求心理的慰藉与平衡,当然除了心理失落所图内容变化外,所处的环境也改变其所绘的景致,江南烟雨成为主要描写的对象,确实没有雄浑的大山了,但情感也变得深沉细腻起来,这时的画家是老了,不复有图壮丽的激情,而只有画平缓优美的一派江南,以图放松自己,借此来渲泻心中淡淡的忧愁。
马麟的《静听松风图》
马远儿子马麟亦是丹青好手,承其父风格,图为马麟的《静听松风图》画一高士卧坐在如虬龙般屈曲蜿蜒的古松下,聆听松风,一童子立其旁。构图形成上下相对的三角形,有一种稳定中不泛动感,远处山丘淡墨渲染,空朦迷离,雾里水滩,也是李唐江南图式的伸延,弱化背景突出松石与主体人物,表现画家的主旨。
马麟此幅作品十分的诗意盎然,想想王维诗云: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李白亦有诗云: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图中高士的罗衣解带虽然尚未露腹,总是袒了胸,放浪形骸之外,此时的松风听来有幽玄奇妙,欣然之思入其怀抱,此风快哉非大王之风非庶民之风,乃为禅意充满的道风。风入松而风为大雅之风,吹入高士之怀亦吹入观者之怀,清风明月一般的不用一钱而得之,只要你有此雅兴,大可披上唐宋时的罗衣,寻一山野松下有流泉处,不必带上童子(大多人无此条件),亦可以体悟古人那种玄远放松的情怀。
图中高士手持的拂尘扔在一旁,风在拂尘埃,吹散心中的尘意,心若不动了,风亦不动了,松亦不动了,万籁俱静,一切进入奇妙的寂灭之境--
对于宋代的绘者来说,图中的境界同样是心象的展示,因为他们的绘山水,不全然是可游可居,重要的还是心灵的故乡的感觉在其中,这些作品谈不上旅游的图鉴,只是绘者用以老来卧游的媒介,或者当事者(绘者)不在时,留下一段心史,让后之来者观看与凭吊,这些作品有喜有悲,而且是喜中有悲,悲中有喜,至少北宋画多是喜中有悲,比如行者观览状态的河山,同样不免因人生短暂,过客而已的悲从心来,这种苍凉的心理,从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南宋的悲中有喜是:比如李唐那幅《采薇图》的情境是:国破了半边,悲则悲矣,总有古代的高士的事迹照亮他们这群半载遗民的心灵。绘画中的云雾法则在宋代绘画中的表现是相当明显的,相当一些的作品是对于云烟与天空是以空白出之,并不作太多的笔墨,但是宋山水画的大部分著名作品是用布面(绢布)本身的成色,加在时代的天然做旧,有一种类似西画色调的感觉,至少比今天宣纸所绘的作品更有这种西画的感觉,绢布泛黄的成色成了一种观者认定的色调,也因而成就今天的观者获得的特别的色彩感觉,事实在古代的观者,比如宋之后的元明清时的观者,亦是有程度不同的感觉。中国古代的绘者对于山水的描绘,有自己约定俗成的一套套路,比如加强山的高峻与深远,会借助云雾的意象,这与现实的实际情形会是相左的。古代的画者,文人为多,所绘的山水画,事实上是另一种诗意的表达,这种奥妙与深刻的程度,确实需要用心体察,不可以忽视的。尤其宋代山水画是在王维文人画创始之后的朝代,他们的艺术理念,会是倾向于文人画,所绘的作者,读书人为多,而且有些绘者,只是绘之,并不以绘师自居,比如李成云:“自古四民不相杂处,吾本儒生,虽游心艺事,然适意而已。”,这个你自然能够联想到后世的石涛也说过“世上独以画师论,摇手非之荡吾胸。”由此说来,宋代绘者视觉感觉类似古代的现实主义山水作品,其实与后世写意的山水绘在心灵感觉上是相同的,皆是心象的展示,既然是心相的展示,那么他们所绘的山水,不是“真”山水,只是心灵的山水,也不能说是“假山水”,只是借助了真山水的形态,而且是主观能动地借助了这种原本纷杂的自然形态,为绘者的心灵服务。对于东方本质的与杰出的绘画作品来说,所绘境界从来不是再现的模仿的境界,而是诗意的,抒情的,表现的境界,是绘者心中的幻相,观者不以观看时以真山水而观看之,而是在流盼作品的过程中,读出其中的情感与诗意来。
我们因此可以觉悟到艺术的真谛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我们仿佛把对象画的很“真实”,其实与现实的真实总是有距离,有取舍,有增减,有安排,有强调与减弱,有虚实,有大小,有阴阳,有向背――,所有这些是因为人为万物之灵的主观元素,在艺术实践的灵活运用,宋代的山水画,借用今天曾经有点左的套话来说,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这里绝对没有唤起诸位文革的艺术记忆的意思,只是想说,宋代的山水绘大师,其实是天然的主观能动性的大师。这样我们再肯定近代大师常常挂在
贵在似与不似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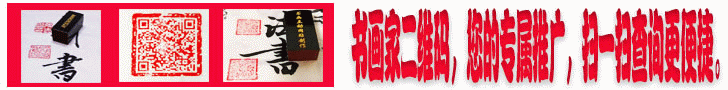




 吉公网安备 22060202000206号
吉公网安备 2206020200020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