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东林党 于 2017-10-5 09:15 编辑
“所有的伟大事物都只能从伟大发端,甚至可以说其开端总是最伟大的。”【1】在王羲之的意识世界中,作为伟大事物的书法的最伟大的开端由两尊巨灵启动——张芝和钟繇,是他们使伟大的篆隶时代成为书法史的“史前史”。孙过庭《书谱》载王羲之语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面对着两尊巨灵,王羲之献上了最虔敬的礼拜,只有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经过他们的托举,他才能够重新启动又一次最伟大的开端,使曾经最伟大的钟、张时代成为书法史的又一“史前史”
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伟大的书《影响的焦虑》的发端:“本书的着眼点仅限于诗人中的强者,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天赋较逊者把前人理想化,而具有较丰富想象力者则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然而,不付出代价者中无所获。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会引起由于受人恩惠而产生的负债的焦虑……诗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2】面对着张芝和钟繇这样最伟大的前辈对手,王羲之无法不产生“影响的焦虑”,这是一种爱、压抑感、竞争欲望、独立意志的奇妙混合,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张芝和怎样的钟繇激起了王羲之的“影响的焦虑”呢?
关于张芝的“考古学”——
张怀瓘《书断》:“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淳化阁帖》卷二所收传为张芝的《冠军》、《终年》、《今欲归》、《二月八日》诸帖至少在形态上颇切合于所谓“一笔书”,姑且悬置气息格调等深度本质问题,直观它们连属飞动的表象,我们可以轻易地还原出一个“快”的张芝。但是,这个“快”的张芝就是完整的张芝吗?
《淳化阁帖》卷二所收最后一件传为张芝的《芝白帖》,米芾鉴定为真迹,黄伯思的态度稍有含混:“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东观余论》)姜夔云:“第五帖章草高古可爱,真伯英之妙迹。”(《绛帖评》)王澍云:“专谨古雅,信是伯英。”(《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对于这件存真度颇高的作品,仍然姑且悬置气息格调等深度本质问题,直观它离散纡徐的表象,我们又可以轻易地还原出一个“慢”张芝:点画运行线路短促,推进凝重,好像大象的脚步,每一次起步和收步之间都保持着从容舒缓的滞空和停顿,沉实地踏下去,然后再悠悠地抬起,周而复始,归根曰静。《芝白帖》唤起了我们对张芝那句怪异得几近不可理喻的箴言的顿悟式共鸣——“匆匆不暇草书”,此正赵壹《非草书》所谓“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卫恒《四体书势》中所描绘的“下笔必为楷则”的张芝显然是这个“慢”的张芝而不是那个“一笔书”的“快”的张芝。
孙过庭《书谱》:“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张芝就仿佛古罗马的两面神亚努斯(Janus),一面是“劲速”,一面是“迟留”,离奇地分裂者。
关于钟繇的“考古学”——
《荐季直表》:除了部分长横以及个别撇和戈的逸出,大体保持着《横方》、《西狭》、《张迁》一路汉隶正面示人、四角收缩齐平的字势,只是在这里,汉隶坚固稳定的方块空间产生了些许轻微的晃动,像是正在学步的短腿婴儿的样子。
《贺捷表》:将《孔宙》一路长裾飘飘的汉隶字势向右上方斜向扯动,标准的方块空间几乎不复存在,点画向四面八方轻盈地散逸开来,空间在流动,或者说,在游动,“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
钟繇——另一个雅努斯(Janus),一面是平画宽结,一面是斜画紧结,亦是离奇地分裂着。
(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评王羲之书语·杜萌若书选自《杜萌若书法集》)
王羲之面对着的最伟大的前辈对手就是这样离奇地分裂着的张芝和钟繇,两尊巨灵分别盘踞在后篆隶时代草书与真书的开端,就如同开天辟地的盘古,他们享受着从各自统领界域的一个端点跳跃到另一个端点的无尽自由,离奇的分裂意味着他们拥有最伟大的强力,看起来,他们是不可战胜的。
王羲之眺望着两位对手,眺望着他们从各自统领界域的一个端点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那般自由、那般有力、那般不可战胜,他的机会在哪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光照亮了那片界域两个端点之间巨大而空旷的中界地带,两尊巨灵的“阿喀琉斯之踵”裸露在王羲之的目光下,他的机会出现了——叩其两端,取其中。
《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程颐注:“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张芝与钟繇离奇的分裂堪称书法史上最伟大的“偏执”之道,王羲之要实现的伟业是将这离奇的分裂最完美地弥合起来,缔造出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中庸”之道——“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张怀瓘《书断》)
草书的命脉系于节奏,张芝的草书或快或慢,各臻其极,凭借精熟之致的功力在两种相反的节奏之间转换自如。如果快与慢的关系摆脱了这样的非此即彼,产生出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此亦彼,草书会变得更迷人吗?
“中庸”的王羲之对抗“偏执”的张芝——
《寒切帖》:点画运行线路之短促一如《芝白帖》,每一个起收段落的滞空和停顿也很清晰,节奏似乎被控制在“迟留”的基调里,但是,《芝白帖》那象步般的凝重推进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蓄势偃卧下压,借势凌空弹跃,顺势骤然回落,一个个瞬间劲疾地爆发或等待爆发,正所谓“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慢”的表象裹住了“快”的内质,这“快”就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有力地挣扎着,渐渐地,“快”变成了表象,而“慢”则变成了内质……之后,又回到了“慢”的表象,“快”的内质……、
《修小园子帖》:很明显的“劲速”的基调,强烈的纵贯意识,可是同样强烈滞空与停顿的潜意识牢牢地牵引着那些轻捷飞翔的悠长线条,执着地把它们凝固成一个个浮雕般的段落,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所谓“风挚红旗冻不翻”之境,或略可仿佛,无论如何,“一笔书”的精神事实上被解构了。
《寒切帖》与《修小园子帖》体现了王羲之草书节奏的两极,然而,相对于张芝草书的离奇的分裂,这两极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大地拉近了,毋宁说,在根本意义上,它们已达成了精神上的统一——“劲速”与“迟留”、“快”与“慢”的辩证互动。
真书的始基本于造型,钟繇的真书或平画宽结、或斜画紧结,互不搭界,处于最天然的自由建构状态。“中庸”的王羲之对抗“偏执”的钟繇,他必将胜利,“真书”的精神必将由“真率”趋向于“真正”,“平”与“斜”、“宽”与“紧”非此即彼的隔绝不通必将被即此亦彼的辩证互动所替代,自由的建构必将导引向纪律的建构。可以说,从王羲之开始,“真书”才真正成为“楷书”,或者说,“正书”。
临摹是王羲之向钟繇致敬的方式,同时也是他对钟繇实施解构的方式。王羲之临钟繇《宣示表》——隐蔽的、温和的解构:大体保持着平画宽结的钟繇短腿婴儿的基本造型,不过,那原本的婴儿已或多或少地儿童化了,学步似的轻微晃动已无踪迹,造型比例有微妙的纵向拉伸,伴随着微微的昂起和较频繁的逸出。王羲之临钟繇《丙舍帖》——赤裸裸的、暴力的解构:既可以说它是平画紧结的,又可以说它是斜画宽结的,在方块空间的基准造型前提下短长斜正的自如伸缩,正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纪律统摄着自由,中和收束着极端。
孙过庭《书谱》载王羲之语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以一敌二,不落下风,王羲之的语气显然是胜利者的语气,可是他的“中庸”气质却使他始终隐忍着最大的骄傲——在行书的领域,他没有真正的敌手,在他的意识世界中,作为伟大事物的行书的最伟大的开端其实是由他本人启动的。
行书介乎真、草之间,介乎真书的造型始基和草书的节奏命脉之间,是最具“中庸”意味的书体,因此,行书与王羲之有着天然的契合,王羲之的本质就是行书的本质,王羲之的草书和真书本质上都是行书。唐太宗《晋书·王羲之传论》赞曰:“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功,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这个“尽善尽美”的王羲之在正式开启行书之门的那一刻,便与书法本质最高贵的圣灵融为一体,成为书法的上帝——唯一的神。
神学家汉斯·昆与另一位神学家卡尔·巴特对话关于莫扎特的问题:“这位将上帝视为‘全然的另一位’(totaliter aliter)的神学家,甚至对热爱上帝的莫扎特也不愿使用‘神性的’这个限定词……但是,如果并非神性的,那又是什么呢?”【3】是的,如果王羲之并非神性的,那又是什么呢?神样的王羲之通达了书法美的中道的极致,“美,超脱宿怨”,【4】两尊巨灵张芝与钟繇的“影响的焦虑”永恒地压迫着王羲之,可永恒的超脱也是不可思议地如影随形般存在着,“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焦虑与超脱——叩其两端,取其中,这就是永恒的“中庸”的王羲之。
王羲之成为绝对意义上书法史的第一位最高立法者,法的精神便是中道的精神,出于世俗的立场,我们尊奉他为书法的王,在书法的王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王与王子是至亲,也是天敌,不想成为王的王子不是好王子。对于书法史而言幸运的是,王献之是好王子,这个好王子无时无刻不处于异常巨大的父王“影响的焦虑”之下,他期待着、酝酿着、并最终真正展开了一场“势均力敌的强者之间的战争,是父亲和儿子作为强大的对手相互展开的战争:犹如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相逢在十字路口。”【5】
书法史上这场最伟大的王与王子的战争以“二王”并立的结果换来了充满紧张感的和平:王羲之失去了王的唯一性,从王降格为“大王”,王献之赢得了王的一席之地,从王子升格为“小王”,但是,“大王”仍旧俯视着“小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庄子·逍遥游》),小王亦不及“大王”。
孙过庭《书谱》载:“(谢)安尝问子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王献之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小王”的命运,忿怨不平,因为神样的看似不可战胜的父亲的“阿喀琉斯之踵”已然裸露在他的目光下——“一种对生命体的丰富性的压制就蕴含于其中,尺度成为主人……厌恶过于有生命力的东西”。【6】分别位居真、草的源头,钟繇和张芝意味着最充沛丰盈的活水最热烈澎湃的涌动,那的确是“过于有生命力的东西”,而在王羲之的意识世界中,“过犹不及”,“中庸”之道的“尽善尽美”必须要以牺牲掉那溢出尺度的丰富和活力为代价,这个代价使王羲之“绝对完美”的立法在气质上显得过于森严、甚至压抑,这难道不形成了一种悖论式的“中庸”之道的“过犹不及”吗?
王献之的机会出现了——一如王羲之的叩其两端、取其中,只是两端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这里,一端是“中庸”的最高立法者王羲之,一端是“偏执”的最高自由者张芝和钟繇,“中庸”之道的正题极致与“偏执”之道的反题极致会通混合,形成或者偏于“过”、或者偏于“不及”的扬弃了的“中庸”之道的崭新合题。
小王的“新法”——
《鸭头丸帖》:张芝“一笔书”精神的复活,大王行草“劲速”与“迟留”的深度平衡被打破,纵贯与连绵淹没了滞空与停顿,“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张怀瓘《书断》),“其锋不可当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张怀瓘《六体书论》)。这自然是偏于“快”的小王,不过,滞空与停顿只是被淹没了,却并非真的消亡,尽管于起收之际几乎不见踪影,实则深隐地潜伏到了连属飞动的线条的每一个毛孔当中,“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唐太宗《大唐三宗圣教序》),这样,更准确地说,张芝“一笔书”的精神在这里只是有条件、有限制地复活,张芝的“快”的极致与王羲之的快、慢之间调合出了一个节奏的平均值,王羲之行草标志性的段落感遭到解构的同时,张芝大草中“过于有生命力的东西”的溢出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了。
《廿九日帖》:张芝《芝白帖》“慢”的极致与王羲之《寒切帖》的快、慢之间调合出了一个节奏上的平均值,钟繇《荐季直表》、《贺捷表》的“真率”与王羲之临钟繇《宣示表》、《丙舍帖》的“真正”调合出了一个造型上的平均值,草书节奏与真书造型两个新的平均值无间然地融为一体。
小王“新法”的要旨在于松弛——一种坦然地从大王“旧法”“尽美尽善”的极致中解脱出来的松弛。传说中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兰亭序》正是传承了松弛的小王“新法”的“小王子”。假手于“小王子”《兰亭序》,小王完成了书法史上最伟大的弑父仪式,《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的名号在世俗的意义上喜剧性地宣告着——上帝死了。
注释:
【1】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M】. 熊伟王庆节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17.
【2】 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8.
【3】 汉斯·昆.《莫扎特:超验的踪迹》.朱雁冰译. 载刘小枫选编《论莫扎特》【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9.
【4】 王浩. 《哥德尔》【M】. 康宏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9.
【5】 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8.
【6】 尼采. 《权力意志》(上卷)【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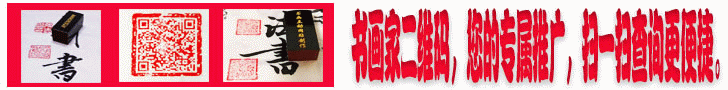






 吉公网安备 22060202000206号
吉公网安备 2206020200020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