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诗炼字四大法则
积字成句,积句成篇。佳篇字句皆好,字句好未必成佳篇,足见吟诗填词锤词炼句之重要。薛雪《一瓢诗话》云:“篇中炼句,句中炼字,炼得篇中之意工到,则气韵清高深渺,格律雅健雄豪,无所不有,诗文之能事毕矣。”诗词用字颇有讲究,现参考诸家之说,略陈用字之祟尚: 曰准,曰雅,曰活,曰新。
一、准
提笔下字,首先要考虑的是准确地描写对象,传情达意。然字有实有虛,实字雅健,虚字贯通,皆须择而用之。实字如名、动、形容,乃骨骼肌体,支撑形象;虚字如副、介、连、助,乃筋脉气息,牵系联带。实字健,宜多;虛字弱,宜少。善用者虚实配合,生机勃勃,顾盼神飞。
岑参“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征》),“然”“捣”二实字健举。李商隐“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已”“更”二虚字空际传神。
再看古人炼字使稳的例子。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云:
王荆公编《百家诗选》,从宋次道借本,中间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复定为“赴”字,以语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谁不能到?”次道以为然。
按:“暝色赴春愁”系唐皇甫冉诗句,原诗《归渡洛水》:
暝色赴春愁,归人南渡头。
渚烟空翠合,滩月碎光流。
澧浦饶芳草,沧浪有钓舟。
谁知放歌客,此意正悠悠。
诗写渡洛水的情景,“赴”字显示春愁浩荡,连绵不绝,若用“起”字便显薄弱。
又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孟浩然”条云:
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石成金也。浩然云“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澹”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二字,亦乌得而为佳句哉?如《六一居士诗话》云“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云: 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论,各以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 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余谓陈公所补数字不工,而老杜一“过”字为工也。
其他如——
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句,“绿”字经反复推敲乃定;
“麦涨一川云”(《题齐安壁》)句,“涨”字何等生机!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境界全出,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境界全出。皆炼字出色之表现。
近代诗人汪石青善用动词,准确传神,如“酌罢葡萄酒一卮,清风沁到半醺时。吟余叱起花间月,照入帘栊瘦似诗”(《月下作》)。“沁”、“叱”二字传神。
“秋风生白露,春梦蚀红颜”(《病》)之“蚀”字,“柏叶迎风簪旧俗,海花入座照良缘”(《剑门以岁首见怀诗惠寄次韵和之》)之“簪”“照”二字,“一灯煮梦夜迢迢”(《秋育》)之“煮”字,皆活泼生动,新颖传神。
有人作绝句《夏天喜雨》云:“酷暑天阴骤起风,频频雷电震长空。甘霖普降农家喜,又是金秋五谷丰。”“又是金秋”与诗题“夏天”错位,我以为改“是”为“兆”方准。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失败后,清廷大臣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在日本春帆楼同日方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安徽某诗人填一词《满江红·甲午之战百廿周年》咏此事,上片结云:“春帆楼,一纸失金瓯,同呜咽。”我觉得“失金瓯”不符合实际,改为“裂金瓯”较妥。
二、雅
雅即高雅,脱却卑俗凡近,立意要高,用字要雅。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一云 :
用字宜雅不宜俗,宜稳不宜险,宜秀不宜笨。一字之工,未足庇其全首;一字之病,便足累其通篇,下笔时最当斟酌。
今有人作《赏海棠》绝句云:
粉面娇容映绿池,丰姿俏丽孕清奇。
繁华自在风神秀,落蕊飞扬香满蹊。
“粉面娇容”“丰姿俏丽”“风神秀”,用语皆俗,而且空洞。前三句的意思第一句已经说尽,语意重复。该诗立意平凡,造语、用字皆俗不入调,却选登在权威性的诗词刊物上,说明有些编辑的欣赏趣味值得反思。
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云:
诗忌粗俗字,然用之在人,饰以颜色,不失为佳句。譬诸富家厨中,或得野蔬,以五味调和,而味自别,大异贫家矣。
比较口语化的俗语俗字,用在曲中尚可,诗词中宜慎用或不用。试读前人名篇佳作,选词用字大抵高雅,口语、俗字尽量少用。
今之作者张口摇笔即来,率尔为篇,立意不高,语言更是俗不可耐,翻翻各地的诗词刊物,此类作品触目皆是。就拿当代颇有成就的“杂文诗派”的诗人来说,他们尝试以口语、俗语入诗,也是失大于得。
如聂绀弩的“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数来三十多三个,一路欢呼满载归”,“何处飞来一石咚”,“多谈几句顶瓜瓜”;杨宪益的“反道人民素质孬”,“屁渣算个啥东西”;李汝伦的“光焰长何万丈呀”,“笔端纸尾祸之妈”,“维纳斯们离画幅……君子观来肉未麻”;邵燕祥的“大会开得很好嘛”。其中的“了”“么”“咚”“顶瓜瓜”“孬”“啥”“呀”“妈”“肉麻”“嘛”等词多具打油味,有些油腔滑调,不伦不类。在聂绀弩那里,一些极难入诗的粗俗语、不登大雅之堂之物,也被拿来入诗,真是艺高人胆大,如“口中淡出鸟来无”,“枯对半天无鸟事”,“红心大干管他妈”,“儿直涂壁书忘八,车马争途骂别三”等等。
口语、俗语好懂,有生活气息,但不易入诗,如何与文言相协调,如何避免庸俗、油滑,运用之妙存于一心。
三、活
诗词以意为主,兴会意到,字句随之,自然活泼,无须刻意搜寻,此就大体言之。但有时必得反复推敲,精心修改,“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才使声情俱佳,惬心贵当。袁枚《随园诗话》卷四云:
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余祝尹文端公寿云:“休夸与佛同日生,转恐恩荣佛尚差。”公嫌“恩”字与佛不切,应改“光”字。《咏落花》云:“无言独自下空山。”邱浩亭云:“空山是落叶,非落花也,应改‘春’字。”《送皇宫保巡边》云:“秋色玉门凉。”蒋心余云:“‘门’字不响,应改‘关’。”《赠乐清张令》云:“我惭灵运称山贼。”刘霞裳云:“‘称’字不亮,应改‘呼’字。”凡此类,余从谏如流,不待其词之毕也。
袁简斋所改前二例,因准而活,所改后二例,因响而活。劝其改者不愧为一字师!
字眼要活。
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炼篇、炼章、炼句、炼字,总之所贵乎炼者,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夫活,亦在乎认取诗眼而已。诗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数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数句为眼者,有以一句为眼者,有以一二字为眼者。”炼字,重在“以一二字为眼”,且欲使活。
李商隐《锦瑟》一诗,解说纷纭,莫衷一是,薛雪《一瓢诗话》云:“如此一首诗全在起句‘无端’二字,通体妙处,俱从此出。”如此,“无端”当为《锦瑟》起句字眼,亦是诗眼,精神凝聚之处。
古人炼字,常于字眼上炼,而字眼无有定处。
字眼在第二字者,如“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杜甫《李监宅》),“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杜甫《晴二首》);
字眼在第三字者,如“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杜牧《旅宿》),“渚云低暗渡,关月冷相随”(崔涂《孤雁》);
字眼在第五字者,如“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钱起《送僧归日本》),“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此类字眼赋予诗句以生机,以神情。
又有词的活用亦可称为活。词的活用使诗句新鲜活泼,生动传神,诗词中常见。
如名词活用作动词,“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四),“巢”本为名词,指鸟巢,这里活用为动词,意即“筑巢栖息”。
动词的使动用法,如“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惊风雨”,即使风雨受惊,“泣鬼神”,即使鬼神哭泣。
形容词活用作动词,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绿江南岸”,意即“使江南岸绿”。
形容词活用作名词,如“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杜甫《放船》),“青”,形容词,这里指青色的事物,“黄”,形容词,这里指黄色的事物。这一联应该理解成: 青色的过去了,是让人怜惜峰峦;黄色的到来了,客人知道是橘柚。
四、新
新,即新鲜,陌生化,力避陈俗。陈言务去,避免那些用滥了的陈词套语,诸如“罗帷”“翠袖”“银釭”“劫灰”“更漏”“雁字”等。还有那些空洞无力的词语,诸如“锦绣”“辉煌”“烂漫”“新气象”“起宏图”“乐悠悠”等,也尽量少用或不用。
避俗的同时要求新。字是现成的平常字,无须生造,关键只在如何运用。
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其用字多新奇峭拔,坚劲有力。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谢榛称“句法森严,‘涌’字尤奇”。又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坼”字、“浮”字也新奇有力。
李贺作诗力避俗语、俗意,“思牵今夜肠应直”(《秋来》),不着眼回肠、曲肠,而说曲肠几乎要变直了,形容用心劳苦之甚,一“直”字迥不犹人。
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次北固山下》),“生”字、“入”字亦新。
王维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中的“冷”字,反常合道,写出感觉真实,是“诗家语”,有新意。个中意味,值得揣摩。
钟振振有一首咏江南水乡的七绝:“曙气红洇麦烟绿,云英紫间菜花黄。四邻长啭嘤嘤鸟,一镇都飘淡淡香。”首句描画出色,新在一“洇”字。试看: 清晨,曙光初照,麦田上飘浮着淡青色的薄烟,红色的曙光缓缓渗透淡青色的薄烟,颇具水彩画的韵味。“洇”字新鲜,生动(钟振振《旧体诗词创作杂谈》)。
此外,关于新词入诗,也应该允许尝试。新词及外来语涉及新的题材、新的形象、新的内容,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气息,可以开拓诗的表现领域,也会增强旧体诗的魅力。但是,作为初学,我们还是先从传统入手比较好,新词入诗,当是今后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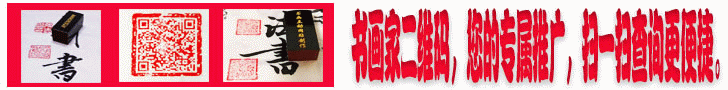


 吉公网安备 22060202000206号
吉公网安备 22060202000206号